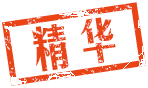|
|

楼主 |
发表于 2012-3-19 10:47:14
|
显示全部楼层
伊豆的舞女(二)
一听是大岛,我的诗意更浓了,我又望了望舞女漂亮的黑发,问了大岛的种种情况。“有许多学生来游泳呢。”舞女对女伴说道。“是在夏天吧?”我说着回过头去。舞女慌了神,小声回答道:“冬天也……”“冬天?”舞女仍旧望着女伴笑了一笑。“冬天也能游泳吗?”我又问了一遍,舞女脸涨得绯红,表情严肃地轻轻点了点头。“真傻,这孩子。”四十岁的女人笑着说道。到汤野去,得沿着河津川的溪谷顺流而下十多公里。越过山岭之后,山峦和天穹的色泽
都使人想起了南国的旖旎风光。我和那汉子谈个不停,完全亲密无间了。等过了获乘、梨本等小村庄,便可以望见山麓下汤野的茅草屋顶了。这时候,我下决心说要同他们一起旅行到下田。他听了喜出望外。
到了汤野的小客栈前面,四十岁的女人脸上露出向我道别的神情时,汉子就替我说道:“他说要和我们结伴同行呢。 ”“那敢情好。常言道:‘出门靠旅伴,处世靠人缘。’像我们这样微不足道的人让您解解
闷还是可以的。那就请进来休息一下吧。”她漫不经心地回答道。姑娘们一同看了我一眼,显出毫无所谓的样子,并不言语,只羞羞答答地望着我。
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栈的二楼,把行李卸了下来。铺席和隔扇又旧又脏。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。她坐到我的面前,双颊一下子涨得通红,手哆嗦个不停,茶碗险些从茶托上滑落下来,于是她顺势放在铺席上,茶却已经洒了出来。见她竟这样羞涩难当,我不禁愣住了。
“真德行!这孩子情窦开啦。哎呀呀……”四十岁的女人万分惊讶似的蹙紧眉头,把手巾扔了过来。舞女拾起手巾,窘迫地擦了擦铺席。听了这番出乎意外的话,我蓦地想到自己。我感到在山岭上被老大娘煽起的幻想骤然破碎了。这时候,四十岁的女人细细端详着我,突然说道:“这位书生穿的藏青地碎白花纹上衣可
真不错啊。”“他穿的碎白花纹上衣和民次穿的花纹是一样的。你说是吧?花纹不是一样的吗?”她反复询问身旁的女人,然后又对我说道:“我在老家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,现在想起他
来了。你穿的碎白花纹上衣和我那孩子的是一模一样的。近来藏青地碎白花纹布贵得很,真为难啊。”“上什么学校?”
“普通小学五年级。 ”
“欸,普通小学五年级,实在……”
“上的是甲府的学校。我长年住在大岛,老家却是甲斐的甲府。 ”
休息了一小时之后,那汉子把我领到另一家温泉旅馆。直到那时为止,我满心以为将和艺人们一同住在这家小客栈里。我们离开大街走过一百多米的碎石路和石台阶,过了小河岸边公共浴场旁的一座桥,桥对面便是温泉旅馆的庭院了。
我进入旅馆的室内浴池,那汉子也跟着进来了。他说,他快二十四岁了,老婆两次怀孕,可不是流产,就是早产,孩子死了。因为他穿着印有长冈温泉商号的短褂,所以我原以为他是长冈人。而且从他的相貌和谈吐来看,他是相当有知识的,我便想象着他是出于好奇,或者是迷恋上了卖艺的姑娘,才帮忙拿着行李一路跟来的。
洗完澡我立即吃午饭。早晨八点钟离开的汤岛,这时还不到下午三点钟。
那汉子临走时,从庭院里抬头望着我,和我寒暄了几句。
“拿这个买些柿子吃吧。对不起,我不下楼啦。”说着,我把一包钱扔了下去。他谢绝了,想要走过去,但是纸包已经落在庭院里了,他只好回转身子拾了起来。
“这可不行啊。”他说着把纸包抛了上来。纸包落在茅草屋顶上。我又扔了下去,他就拿走了。
傍晚时分,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。群山被染成白茫茫的一片,远近层次迷蒙难辨,前面的小河也霎时间变得混浊昏黄,流水声越发响亮。我想,这么大的雨,舞女们不会来演出了吧,可是我坐不住,又去了两三次浴池。房间里暗沉沉的。与邻室相隔的隔扇上开了一个四方的洞,门楣上吊着一盏电灯,两个房间共用着一盏灯。
咚咚咚咚,在骤雨声中,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了鼓声。我几乎要把窗板抓破似的打开了它,探出身子去。鼓声似乎更近了。风雨击打着我的头。我闭上眼睛侧耳倾听,想知道这鼓声从哪里来,是怎么来的。不久,传来了三弦的声音,传来了女人的呼喊声,还有闹哄哄的欢笑声。我明白了,艺人们被叫到小客栈对面的饭馆里,在宴会上演出去了。可以辨出两三个女人和三四个男人的声音。我期待着那边结束后,她们会到这边来。可是那场酒宴热闹非凡,看样子要一直闹腾下去。女人的尖叫声不时像闪电一般刺破黑夜。我神经紧张,始终敞开门窗,一动不动地坐着。每当听到鼓声,心里就畅快了。
“啊,舞女还坐在宴席上。她坐着敲鼓呢。 ”
鼓声一停我就无法忍受,迷失在雨声中。
过了一会儿,不知道是大家在追逐嬉戏呢,还是在绕着圈跳舞,纷乱的脚步声持续了好一阵子。然后,一切又突然重归于寂静。我睁大眼睛,想透过黑暗看清这片寂静意味着什么。我十分苦恼,心想,舞女今天晚上会不会被玷污呢?
我关上窗板,钻进了被窝,可内心仍旧很痛苦。我又去洗澡,暴躁地泼溅着浴水。雨停了,月亮出来了。被雨水冲洗过的秋夜清澄而明净。我想,即使光着脚溜出浴池赶到那边去,也做不了什么。这时已经是两点多钟了。
第三章
次日早晨九点多钟,那汉子就来到我的宿处。我刚刚起床,邀他一同去洗澡。晴空万里的南伊豆正是小阳春天气,涨水的小河在浴池下方沐浴着暄和的阳光。我自己也觉得昨夜的烦恼如梦幻一般,我对那汉子说道:
“昨天晚上热闹得很晚啊。 ”
“怎么,你听见了?”
“当然听见了。 ”
“都是些本地人。这里的人只会瞎折腾,真没意思。 ”
见他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我不言语了。
“那些家伙到对面的浴场来了。——瞧,好像看到我们了,还在笑呢。 ”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我向河对岸的公共浴场望去。在朦胧的水蒸气中,七八个光着的身子若隐若现。
突然,一个裸体的女人从微暗的浴场里跑了出来,站在更衣场凸出的地方,做出要跳到河岸下的姿势,伸展开双臂,嘴里喊着什么。她赤裸裸的,身上连一条手巾也没有。那是舞女。她伸长了双腿,洁白的裸体犹如一株小泡桐似的,我眺望着,感到有一股清泉涌入心田,不禁深深吁了口气,噗哧一声笑了。她是个孩子。她发现了我们,一时喜不自胜,就这样赤身裸体地跑到了阳光底下,踮起脚尖,挺直身子站着。她还是个孩子呢。我心情舒畅地笑个不停,头脑澄清得像刷洗过一样,嘴边久久地荡漾着微笑。
由于舞女的头发非常丰厚,我一直以为她有十七八岁,再加上她被打扮成妙龄少女的模样,所以我完全猜错了。
我和那汉子回到我的房间,不一会儿,那个年长的姑娘到旅馆的庭院里来看菊花圃。舞女走到桥当中。四十岁的女人从公共浴场里出来,望着她们俩。
舞女耸耸肩,像是在说:“会挨骂的,还是回去吧。”便笑了笑,快步往回走去。四十岁的女
人来到桥边,招呼道:“您来玩啊!”“您来玩啊!”年长的姑娘也同样说了一句。她们都回去了。那汉子则一直坐到傍晚。晚上,我正和一个批发纸张的行商下围棋,突然听见旅馆的庭院里传来了鼓声。我想站
起来。“卖艺的来了。 ”“嗯,没意思,那种玩意儿。喂,喂,该你下啦。我下在这儿。”纸商指着棋盘说道,他
完全沉浸在胜负之中了。在我心绪不宁的当口儿,我听见艺人们似乎要回去了,那汉子在庭
院里向我招呼道:“晚上好。”我走到廊下招了招手。艺人们在庭院里相互耳语了几句,然后转到大门口。三个姑娘跟
在那汉子身后,依次说了声“晚上好”,在廊下垂着手,行了个艺妓式的礼。棋盘上瞬间出现
了我的败像。“没法儿了。我认输。 ”“怎么会输呢?是我这方不利嘛。不管哪一步都是细棋。 ”纸商看也不看艺人一眼,逐个数着棋盘上的目数,下得越发谨慎了。姑娘们把鼓和三弦
收拾在房间的角落里,在象棋棋盘上玩起五子棋来。这时我已经输了本该赢的棋,可是纸商仍旧纠缠不休:“怎么样?再下一盘,请再下一盘吧。”但我只是一味地笑着,纸商终于死了心,站起身来走了。
姑娘们向棋盘这边走过来。“今天晚上还要到其他地方演出吗?”“还要去的……”说着,那汉子朝姑娘们望去。“怎么样,今天晚上就到这儿,让大家玩玩吧。 ”“好啊!太高兴了! ”“不会挨骂吧?”“怎么会,反正再走下去也没有客人。 ”于是她们玩起五子棋来,一直玩到十二点多才走。舞女回去之后,我毫无睡意,头脑清醒异常,便走到廊下试着喊道:“老板,老板。 ”“哦……”快六十岁的老大爷从房间里跑出来,精神抖擞地应了一声。
“今天晚上下个通宵。先跟你说好啰。 ”我也变得非常好战了。
第四章
我们约定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从汤野出发。我戴上在公共浴场旁边买来的便帽,把高中制帽塞进书包,向沿街的小客栈走去。二楼的门窗完全敞开着,我无意之中走了上去,只见艺人们还都躺在铺席上。我张皇失措,站在廊下愣住了。
舞女就躺在我脚跟前的铺垫上,她满面绯红,猛然用两只手掌捂住了脸。她和那个较大的姑娘睡在一张铺上,昨晚的浓妆还残留着,嘴唇和眼角微微透出红色。这颇具情趣的睡姿不禁让我心荡神驰。她敏捷地翻了个身,仍旧用手掌遮着脸,从被窝里滑了出来,坐到廊下。
“昨晚上谢谢您了。”她说着利落地行了个礼,我站在那里,被弄得手足无措,不知如何是好。
那汉子和年长的姑娘睡在同一张铺上。在看到这之前,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俩是夫妇。
“真对不起。本来打算今天动身的,但是晚上有个宴会,我们决定推迟一天。要是您今天非动身不可,那就在下田见面吧。我们准备住甲州屋客栈,很容易找到的。”四十岁的女人从铺垫上抬起半截身子说道。我顿时感到像是被人抛弃了似的。
“明天再走不好吗?我不知道妈妈要推迟一天。路上还是有个伴儿好。明天一起走吧。 ”那汉子说完后,四十岁的女人接着说道:
“就这么办吧。您特地要和我们同行,我们却擅自决定延期,实在对不起——明天哪怕天上下刀子也要动身。后天是在旅途中死去的小宝宝的断七日。我早就想着要在下田做断七,这么匆匆忙忙赶路,为的就是在那天之前到达下田。跟您讲这些真是失礼了,但我们特别有缘分,后天也请您来参加祭奠吧。 ”
于是我决定推迟一天出发,走到了楼下。我一边等大家起床,一边在肮脏的账房里跟客栈的人聊天,那汉子邀我出去散步。沿着大街稍稍往南走,有一座很漂亮的小桥。靠在桥栏杆上,他又谈起了自己的身世。他说,他有段时间参加了东京的一个新派剧剧团。现在还经常在大岛港演出。从他们的包袱里像一条腿似的伸出来的就是刀鞘。他还在宴会上模仿新派剧。
柳条包里装着戏装和锅碗瓢盆之类的生活用品。“我最后落到这步田地,耽误了前程,但我的哥哥在甲府出色地继承了家业。所以我是
一个多余的人了。 ”“我一直以为你是长冈温泉的人呢。 ”“是吗。那个年长的姑娘是我老婆。她比你小一岁,十九岁了。在旅途上第二个孩子早
产,没过一星期孩子就断了气,我老婆身体还没有复原。妈妈是我老婆自己的母亲。舞女是
我的亲妹妹。”“哦,你说你有个十四岁的妹妹……”“就是她呀。我实在不想让妹妹干这种营生,但是这里面还有许多缘故。 ”然后他告诉我,他本人叫荣吉,妻子叫千代子,妹妹叫熏。另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叫百合
子,只有她是大岛人,雇来的。荣吉显得非常伤感,哭丧着脸,久久凝视着河滩。我们回来的时候,看见洗去脂粉的舞女正蹲在路旁,抚摸着小狗的脑袋。我想回自己的
旅馆去,便说道:“来玩吧!”“唉。可是一个人……”“和你哥哥一起来嘛。 ”“马上就来。”不多久,荣吉来到我的旅馆。“她们呢?”“她们怕妈妈唠叨。 ”但是,我们才玩了一会儿五子棋,姑娘们就过了桥,噔噔地跑上二楼来。像往常一样,
她们恭敬地行了个礼,跪坐在廊下,踌躇不前,千代子第一个站起身来。“这是我的房间。来,请不要客气,进来吧。 ”玩了一个小时左右,艺人们到这家旅馆的室内浴池洗澡去了。她们再三邀我同去,可是
有三个年轻女人在,我便搪塞说,我过一会儿再去。舞女很快一个人跑上楼来,转告千代子
的话说道:“嫂嫂说,请你去,她给你搓背。 ”我没去浴池,和舞女下起五子棋来。她下得出奇地好。循环赛的时候,我不费吹灰之力
就打败了荣吉和其他女人。下五子棋,我得心应手,一般人决不是我的对手。而跟她下棋,用不着特地留一手,心情很畅快。 |
|